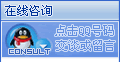近年來,“性騷擾”案例不斷激增,“性騷擾”現象逐漸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
北京市人大常委會5月21日審議《北京市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辦法(修訂草案)》,將向女性發(fā)送黃色短信、濫講黃段子、有肢體行為等行為被確定為“性騷擾”。
草案在第38條明文規(guī)定:禁止以語言、文字、圖像、電子信息、肢體行為等任何形式對婦女實施性騷擾。遭受性騷擾的婦女,可向本人所在單位、行為人所在單位、婦女聯(lián)合會和有關機構投訴,也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訴。
草案還對性騷擾的形式進行了界定,明確了用人單位、公共場所管理經營單位應當根據情況采取措施,預防和制止對婦女實行性騷擾的行為。
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性騷擾的詞匯開始蔓延開來,至于性騷擾的標準也一直沒有定論,而且最為主要的一點是取證上的困難,按照民事訴訟當中 “誰主張,誰舉證”的舉證責任原則,使得原告通常出于非常被動的地位,由于性騷擾一般發(fā)生在不公開私密的情況下,很多都是兩個人單獨相處的時候,言語和身體接觸很難留下證據,造成即便是告上法庭也很難取證。
有人提出在性騷擾案件中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的觀點。人們對于性騷擾實施者的痛恨與對受害人的同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認為,性騷擾案件在某種程度上說,不加任何條件的讓“加害人”承擔證明其沒有實施性騷擾行為的責任,其難度并不比“受害人”證明“加害人”實施了性騷擾行為小。如果要讓被告方舉證自己沒有實施性騷擾的行為也是不太妥當,還是應該由受害人承擔舉證責任,對于其面臨的舉證困難問題,解決的辦法不在舉證責任的分配上,而是應當通過降低證明標準的方式來加以緩解。
建議人民法院在審理案件中,相應證據規(guī)則應該做變通。比方說在舉證責任問題上,由于性騷擾的隱蔽性、突發(fā)性特點,是否可以對“誰主張誰舉證”這樣的規(guī)則做證據責任的合理轉移。“就是說當原告舉出的證據達到了一個初步可信的程度的話,那么法院應當要求被告提出一個辯駁性的證據。在被告不能提出辯駁性的前提下,那么法院就可以認定原告的主張是成立的。
從世界范圍內看,性,正在發(fā)生或正在經歷著從道德到權利、從人倫到人權的轉化。人權運動、婦女解放、女權主義、性別革命等等,使得性與權利、人權密切結合,逐步走向性的“人權本位”。性在這里已經超越了一般所理解的狹義的“性交”,被構建為人的“本質”與“人格”的一部分。面對性的人權化走向,面對人權已經入憲,面對“21世紀的文明風暴”,作為解決糾紛、化解社會風險的中國民事訴訟應當對于性騷擾案件有所作為,以維護受害人被侵犯的合法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