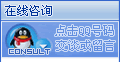根本違約制度起源于英國判例法,19世紀英國法院開始把合同的條款劃分為“條件”和“擔保”兩類,“條件”是合同中重要的、根本性的條款,“擔保”則是合同中次要的和附屬性的條款,當事人違反不同的條款,所產(chǎn)生的法律后果是不同的。一方當事人違反“條件”,另一方當事人不僅可以要求賠償,而且有權解除合同;一方當事人違反“擔保”,另一方只能請求賠償而不能解除合同。法官在論述違反“條件”時,使用了“本質上違反合同”、“根本上沒有履行合同”、“動搖了合同根基”等提法,這是英國判例法中“根本違約”一詞的源出。到本世紀50年代,英國法官試圖運用根本違約來排除各種不公平的免責條款的使用,他們主張如果一方違反合同義務以致動搖了合同的根本時,則不得利用合同中的免責條款逃避違約或侵權責任。而違反“條件”理論使當事人和法院可以比較容易地對違約能否導致合同解除作出判斷,但是,根據(jù)這一理論,即使對方處在并未因此遭受損害或損害極其輕微的情況下,違反“條件”一方當事人也可能承受來自對方解除合同的后果。到了二十世紀,格式合同的出現(xiàn)和普遍運用使契約自由受到極大限制,格式合同中的免責條款經(jīng)常規(guī)定“不論實際情況如何,該組織概不負責”,這是明顯違背公平原則的,于是,到20世紀60年代,英國法院對違反“條件”理論進行了重大變革,在契約自由與禁止濫用免責條款之間尋求某種公平的衡平制度[1]。英國法開始以違約后果為根據(jù)來區(qū)分不同的條款,認為“違反某些條款的后果取決于違約所產(chǎn)生的后果”,違約違反的是屬于條件還是擔保條款,主要取決于違約事件是否剝奪了無辜當事人“在合同正常履行情況下本來應該得到的實質性利益”。這實際上反映的是“條件”和“擔保”以外的第三種條款,即所謂“中間條款”。“中間條款”理論的出現(xiàn)為法官根據(jù)違約造成的客觀后果而不是根據(jù)被違反條款的性質來斷定當事人一方是否有權因對方違約而解除合同提供了一個新的標準和思維方法。此時,根本違約已不再是違反條件的同義語,而是指任何足以使受害方有權解除合同的違約行為。
美國法與英國法不同,沒有使用“根本違約”的概念,而是采用“重大違約(materialbreach)”或“根本性不履行(substantialnon-performance)”概念,把違約分為輕微違約和重大違約,一般只有構成重大違約,非違約方才有解除合同的權利之可能(因為有時即使構成重大違約,非違約方也不能立即解除合同,而應先給予違約方充分的自行救濟機會)。但實質上這一標準不適用于貨物買賣合同,如果貨物或提示交付的單據(jù)在任何方面不符合合同,即使輕微違約,除非當事人另有約定,買方可以全部拒收貨物(《美國統(tǒng)一商法典》第2—601條)。至于是否構成重大違約,《美國合同法重述(第2次)》第241條規(guī)定的主要考慮因素是:(1)受損害方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他從合同中應得到的合理預期的利益;(2)受損害一方的損失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適當補救的;(3)如果受損害一方終止履行,有過失一方在多大程度上會遭受侵害;(4)有過失一方彌補過失可信度;(5)有過失一方的行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善意”與“公平交易”準則[2]。那么,法官在判案中認定根本違約時如何適用呢?是只具備其中一個因素即可,還是同時具備五個因素才行呢?有沒有一個份量比較重呢?紐約州上訴法院法官西巴黎克(Ciparick)在最近一個案例中指出,是否適用“嚴重違反合同”理論,首先要看有過失一方會不會遭到難以承受的重大損害(即第3種因素)[3],而有的學者則認為美國法院在判定重大違約時考慮的最重要的因素是違約的受損害方有權期待從交易中獲得的利益在多大程度被剝奪了(即第5種因素)[4]。因之,美國的重大違約作為合同解除權的限制條件不具有絕對性,且其判定標準復雜,缺乏明確的適用順序,具有不確定性,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過大,給非違約方利用解除合同進行違約救濟制造了障礙,使其無所適從。
大陸法系并無根本違約的概念和統(tǒng)一標準。《法國民法典》第1184條雖然規(guī)定債權人于債務人一方違約(不論嚴重是否)時可通過法院來解除合同,但是法國法院往往將債權人不履行義務的行為嚴重作為合同解除的一個重要判定標準[5]。《德國民法典》第326條及第326條規(guī)定了給付不能(包括全部給付不能與部分給付不能)、給付遲延(包括定期債務的給付遲延與非定期債務的給付遲延)情形的合同法定解除條件,但其實質是以違約后果的嚴重性(即根本違約)作為判定標準,不過根本違約判定標準系結合具體違約形態(tài)的分析來體現(xiàn)的。顯然,《德國民法典》既未像法國法及英國判例法那樣簡單地界定根本違約的定義,也未像美國那樣抽象地囊括根本違約判定標準的綜合考慮因素,做到形散而神似,將根本違約判定標準之抽象概括(即違約造成的后果嚴重致使合同預期目的的不能實現(xiàn))化解在具體違約場合之下,其立法模式更具科學性。
吸納了兩大法系立法成果《聯(lián)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下稱《公約》)使用了“根本違約”一語,并明確規(guī)定了根本違約的標準界定,即“一方當事人違反合同的結果,如使另一方當事人蒙受損害,以至于剝奪了他根據(jù)合同規(guī)定有權期待得到的東西,即為根本違反合同,除非違反合同一方并不預知而且一個同等資格、通情達理的人處于相同情況中也沒有理由預知會發(fā)生這種結果”(第25條)。但是,《公約》第25條規(guī)定的可預見性標準具有不確定性,往往會限制非違約方的合同解除權,使其不敢貿然采取解除合同之違約救濟措施;同時,《公約》第49條、第51條、第64條、第72條、第73條規(guī)定的具體違約判定標準并無《公約》第25條所規(guī)定的可預見性標準之要求,二者之間顯然存在矛盾,這也使得非違約方解除合同予以救濟時往往舉棋不定。
在我國已失效的《中國涉外經(jīng)濟合同法》第29條規(guī)定:合同一方當事人違反合同,以致嚴重影響訂立合同所期望的經(jīng)濟利益或合同一方當事人在約定的期限內沒有履行合同,而且在被允許推遲履行的合理期限內仍未履行的,另一方有權解除合同。與《公約》相比較,我國涉外合同法拋棄了主觀標準,沒有使用預見性理論來限定根本違約的構成,減少了因主觀標準的介入而造成的隨意性以及對債權人保護不利的因素。另外,在違約的嚴重性的判定上,涉外合同法采用了“嚴重影響”的概念來強調違約結果的嚴重程度,而沒有使用“實際上”剝奪另一方根據(jù)合同有權期待得到的東西,這就使判斷根本違約的標準更為寬松。實踐證明這種規(guī)定是切實的、合理的[6]。在借鑒和吸收包括《涉外經(jīng)濟合同法》在內的三部合同法經(jīng)驗的基礎上制定的中國統(tǒng)一合同法,關于根本違約的規(guī)定又比《涉外經(jīng)濟合同法》更為合理。該法第94條第4款規(guī)定:“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債務或者有其他違約行為致使不能實現(xiàn)合同目的”,另一方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盡管在此規(guī)定中并沒有使用根本違約的概念,但已充分體現(xiàn)根本違約制度的思想。“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債務或者有其他違約行為致使不能實現(xiàn)合同目的”強調了“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債務或者有其他違約行為”的嚴重后果是“致使不能實現(xiàn)合同目的”。“致使不能實現(xiàn)合同目的”是從違約后果的嚴重性出發(fā)來判斷是否為根本違約。同時,該條還規(guī)定了:在履行期限屆滿之前,當事人一方明確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主要債務,經(jīng)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內仍未履行,以上解除合同的情形均可以歸納為違約所造成的結果嚴重,使合同目的落空或不可期待,實即根本違約。
但是,我國《合同法》雖在分則的買賣合同、承攬合同等有名合同中規(guī)定了瑕疵履行及部分違約的根本違約適用標準,但這些規(guī)定顯然不能適用于所有的合同類型。民法作為行為規(guī)范和裁判規(guī)范,具有引導、規(guī)范人們日常行為模式之功能,《合同法》第94條第4款“其他違約行為致使不能實現(xiàn)合同目的”之規(guī)定,缺乏操作性且未考慮不同違約形態(tài)之個性差異,過分抽象、模糊的法律語言顯然難以勝任這一功能。因此,應將拒絕履行、瑕疵履行及部分違約情形的根本違約判定標準補充到《合同法》的合同法定解除制度中,既便于人們日常民商事交往的合理行為預期安排,又能使法官裁判具有確定性的依據(jù)。
筆者認為根本違約判定標準應脫掉其抽象外衣,結合具體違約形態(tài)來分析合同法定解除權之合理行使,界定根本違約的具體判定標準。根據(jù)合同目的是預期還是實際不能實現(xiàn)、是部分還是全部不能實現(xiàn)之標準,結合具體違約形態(tài)對根本違約具體判定標準可作如下類型分析:
1. 預期根本違約判定標準。預期違約,包括明示預期違約和默示預期違約,是英美法系特有的法律制度。大陸法系無預期違約概念,而有與默示預期違約規(guī)則相類似的不安抗辯規(guī)則,雖然二者在性質、適用范圍、成立條件及權利救濟措施等方面存有差異[7],但仍存在聯(lián)系:一方當事人行使不安抗辯權后,對方的行為狀態(tài)往往是抗辯權人借以推知其是否構成默示預期違約的基本條件之一[8]。正因為如此,兩規(guī)則可同時規(guī)定在同一合同法中。《美國統(tǒng)一商法典》第2—609條規(guī)定即是例證,該條第1項規(guī)定了不安抗辯內容,第4項實質上是默示預期違約制度規(guī)定。我國《合同法》采用了與《美國統(tǒng)一商法典》不同的立法技術,將不安抗辯規(guī)則置于“合同履行”一章,而將預期違約作為違約形態(tài)規(guī)定于合同解除和違約責任的相關章節(jié)。
明示預期違約情形,即合同有效成立后至合同約定的履行期限屆滿前,一方當事人明確肯定地向另一方當事人表示其將不履行合同義務時,便構成根本違約,另一方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默示預期違約情形,預期違約方并未將到期不履行合同義務的意思表示出來,另一方只是根據(jù)預期違約方的某些情況或行為(履行義務的能力有缺陷、商業(yè)信用不佳、準備履行合同或履行合同過程中的行為表明有不能或不會履行的危險等)來預見其將不履行合同義務,此時可以終止自己相應的履行并要求對方在合理的期限內提供其能夠履行的保證;若對方未能在此合理期限內提供履行保證,即構成根本違約,預見方才可以解除合同。
2. 實際根本違約判定標準。實際違約形態(tài)包括履行不能、拒絕履行、遲延履行及瑕疵履行,各種違約形態(tài)的違約程度不一,因此構成根本違約的具體判定標準也不同,有必要再作具體分析:(1)履行不能情形的根本違約判定標準。履行不能是指債務人在客觀上已經(jīng)沒有履行能力,如以特定物為標的的合同,該特定物毀損滅失,以種類物為標的的合同中,種類物全部毀損滅失。履行不能即屬合同目的無論是因債務人之原因,還是因債權人之原因或者不可歸責于雙方當事人之原因不能實現(xiàn),構成根本違約,致合同履行不能債務人或債權人均可解除合同。(2)拒絕履行情形的根本違約判定。拒絕履行是指履行期限屆滿時,債務人能夠履行債務而故意不履行。由于拒絕履行與預期違約在是否可以消除違約狀態(tài)、撤回拒絕履行的意思表示及賠償范圍上存有差異,同時,雖然與遲延履行一樣均違反了履行期限的要求,但是二者在違約當事人的主觀意思、補救方式上顯有區(qū)別,因此應將拒絕履行界定為履行期限屆滿后的故意不履行而與預期違約相區(qū)別。拒絕履行是一種較為嚴重的違約,違約方故意不履行合同使合同目的不能實現(xiàn),當屬根本違約,非違約方此時有權解除合同。(3)遲延履行情形的根本違約判定標準。遲延履行指債務人能夠履行,但在履行期間屆滿時卻未履行債務的現(xiàn)象。構成遲延履行必須具備四要件:存在著有效的債務;能夠履行;債務履行期間已屆滿;債務人未履行。遲延履行包括定期債務的遲延履行和非定期債務的遲延履行。定期債務遲延履行場合,根據(jù)合同性質或者當事人的約定,履行期限是合同履行的根本條件,若當事人一方不在特定時間履行,不能達到合同目的,則構成根本違約,相對方無須催告,即有權解除合同。非定期債務遲延履行場合,根據(jù)合同的性質,履行期限在合同的內容上不特別重要,如果合同一方當事人遲延履行時,相對人應催告其在合理期限內履行債務,如該期限屆滿仍未履行的,說明合同目的不能實現(xiàn),即構成根本違約,相對人有權解除合同。(4)瑕疵履行情形的根本違約判定。瑕疵履行指債務人雖有履行,但其履行(如質量、地點、方式等,履行數(shù)量有瑕疵屬遲延履行)有瑕疵或者給債權人人身、其他財產(chǎn)造成損害,或給與對方債權人有特定關系的第三人的人身或財產(chǎn)造成損害,包括不適當履行和加害給付兩種類型。不適當履行場合的根本違約判定標準,德、法、日等國立法及《公約》、《通則》并無明確規(guī)定,我國臺灣學者史尚寬、王澤鑒主張可類推適用遲延履行及履行不能之根本違約判定標準:不適當履行能夠補正的,債權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補正;如于此期限內仍不補正時,則構成根本違約,債權人可解除合同;惟非于一定時期履行則不能達合同目的者,即為根本違約,可不經(jīng)定期催告而徑直解除合同;履行上的瑕疵不能補正者(如特定標的物已不可能修理),即屬根本違約,債權人可以解除合同。加害給付一經(jīng)發(fā)生,不僅使債權人合同目的不能實現(xiàn),而且對債權人及第三人人身、財產(chǎn)造成損害,當然構成根本違約,債權人有權解除合同[9]。
3.根據(jù)合同目的不能實現(xiàn)的程度不同,根本違約又可分為全部根本違約與部分根本違約。前者是指致使合同目的全部不能實現(xiàn)的違約行為,后者則指導致合同目的部分不能實現(xiàn)的違約行為。履行不能、拒絕履行、瑕疵履行、遲延履行及預期履行均存在全部違約與部分違約之分。前述各種具體違約形態(tài)根本違約標準之確定,是就全部違約分析而言的。若為部分違約,而合同內容為可分者,致使該合同部分目的不能實現(xiàn),則構成部分根本違約,債權人可就該部分合同予以解除;但合同內容不可分者,部分違約致使合同目的全部不能實現(xiàn),則構成根本違約,債權人可就合同全部予以解除(《德國民法典》第325條第1款第3項、第326條第1款第3項、《意大利民法典》第1464條、《日本民法典》第543條、《公約》第73條)。
當然,根本違約制度的重要意義,主要不在于使債權人在另一方違約的情況下獲得解除合同的機會,而在于嚴格限定解除權的行使,限制一方當事人在對方違約以后濫用解除合同的權利[10]。這一限制是非常有必要的。合同是當事人自由協(xié)商而達成的合意,是當事人籌劃自己的生產(chǎn)、交換和消費等社會生活而進行的行為預期安排。但是如果當事人一方存在違約行為,不論輕微或重大,另一方過分輕易解除合同,不僅對違約方構成重大損害,而且也造成了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根本違約的形式價值在于合理限制合同法定解除權,實質意義在于給予違約方更多的自行救濟機會,避免因輕微違約而遭受不利益,促使社會資源配置效益的最大化,為違約方利益與非違約方利益、非違約方利益與社會利益之沖突尋求一個理想的平衡點。